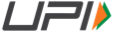9月,搜狐第二屆通訊沙龍隆重舉行。此次,搜狐IT頻道會聚了行業內多位知名專家,共同就電信與互連網的融合中的軟體問題展開了一場智慧交流。來自資訊產業部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、發改委、北京郵電大學的專家,及中國電信、中國鐵通、華為、中興等企業的代表們,共同就通訊應用軟體的產業地位、統一應用軟體發展的政策環境、業務應用對移動軟體的機遇與挑戰等話題展開了充分討論。以下是點擊科技CEO王志東的演講實錄。
王志東:剛開始開會的時候,我聽史煒的報告,就有些心裡沒底,因為今天主題講通訊軟體,並且更多的是跟通訊電訊廠商相關的軟體。以這麼定義的話,我幾乎沒有發言權。但是後來聽著,我覺得還是有話可以講的。主要從兩個方面說一下我的感受。
第一,在今天講的內容裡,很多都提到產業,不僅IT產業,還有軟體產業,還有通訊產業,通訊產業再往下還不夠,還不停地細分。剛才有幾位都說了我們定了很多“產業”,在英文裡查不到,我們為什麼有產業的偏好呢?跟我們有計劃經濟的思維相關。
我們做什麼都想做產業,我們的管理也希望劃分成產業,所以資訊產業部的名字裡都有產業,都想變產業,但實際上現在我們再去看,一說到產業就有產業的定義,產業的劃分,剛才也討論了很多,到底怎麼去分。
我跟大家說一個感受,我最開始接觸風險投資,接觸很多外國銀行分析師的時候,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特點,分析師每年或者每季度有一個分析報告,每一次分析報告對行業分類都有可能不一樣。他的分析報告現在看不到我在分析的這個公司,他是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裡或者跟我沾邊大的範圍裡,這些公司現在處在什麼樣新的動態,有什麼樣新的產品,這個產品出現之後,來幫著分析有哪些相關性,根據相關性,他認為這麼一種分類是最科學的。分類完以後,才講這個代表著什麼趨勢,未來的發展可以做一個預測,會有什麼樣的動向,而且這樣一種動向會對整個的產業生態產生什麼影響。這是分析師基本的分析方法。
這個方法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思路就是我們做分析的,做決策的永遠是落後產業本身的。他們認為在產業裡,最積極,最有革命性,最能夠感知未來的是這些企業,這些企業才是真正領導產業往前走的,他們這些分析師只在旁觀,然後去預測。就跟看跑馬一樣,大家都在跑馬,哪個馬跑得好,哪個跑得壞,只有騎士知道,旁邊跑馬的人只在旁觀做預測,這是分析師的分析方法。
反過來看國內一些政府的報告,或者給政府出報告的人,寫了很多政策,基本的概念就是我們先寫,或者說做很多預測性分析之後,畫出很多界限,做出框框,根據框框制定政策,定完以後,結果變成產業裡的人削尖腦袋裡套進政策來,不套進政策,很多政策拿不到。什麼是軟體產業?現在誰都說自己是軟體產業。上次見了江蘇做冰箱的,他說我這裡軟體產業的比例很大。我說你做冰箱怎麼成做軟體的。他說你看我這裡有一個微處理器,這微處理器就是軟體,我說軟體怎麼算你的價值呢?他說跟領導說了,這台冰箱沒有這個軟體的話就是廢品一堆,有這個軟體,就能賣好價錢了。所以所有增值的部分都是我的軟體價值。他這麼劃分的目的是什嗎?很簡單,定出了產業的產量之後,管政府要退稅。而地方政府明擺著知道這個事情胡扯,但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,為什嗎?因為這個都報上去之後,這是地方的政績,這是在國內很普遍的現象。這一現象是制定的政策框產業往前走或者套產業,或者產業自覺自愿往那個產業去框。這跟外國完全不一樣,主次關係完全是反過來的。這個反過來到底有什麼樣的合理性,有什麼影響,這些東西大家去分析,我就說能看到這個很有趣的現象。
第二,我們一直說軟體產業。軟體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,現在很多都在定義什麼叫軟體,大家都談到過若干。比如看到報告裡有過分析,美國有美國的模式,歐洲有歐洲模式,歐洲甚至可以分法國是什麼軟體模式,日本是什麼模式,印度是什麼模式,中國是什麼模式。既然每個人的軟體都不一樣,我們國內自己發展什麼叫軟體,什麼不叫軟體,這個定義沒有太大的必要,嵌入式叫不叫做軟體,當然叫了。如果我們把叫什麼樣形式這個決定權交給企業的話,企業能掙錢,自然往這個模式上轉。比如大家說google,google是不是軟體?我認為肯定是軟體,但是我跟google的人說,你google最大的價值是什嗎?我以為他會說他是搜尋技術,他說不是,google最大的價值就是我們製造了一個全世界最大型的並行電腦,並行電腦就是自己組裝的PC機,但是用的是30萬,現在說很快能突破一百萬,有一百萬台PC組成的並行的電腦陣列,這個是真正的核心價值。我說一百台機器運行工作都是靠軟體,他說所有的機械都是在超市買的。歸根到底是靠軟體,但是你看google的總收入,剛才問有沒有人為google交過費?我就為google交過費,買過他們的地圖。google的收入是來自於廣告,如果按國內劃分是廣告業。現在在互連網上有這種趨勢,你做的業務和你最終的收入這兩個完全分開的,剝離的,業務在這個產業裡,但是你的收入可能出現在另外一個產業裡,這個時候還用傳統的產業劃分。這些都值得去研究。在軟體方面,比如說原來新浪最早的時候認為最強的是發布軟體,發布系統出去之後,賣發布系統不如做門戶網更值錢,門戶網我們自己運營起來,而不是變成軟體銷售了。運營最終收入進入媒體,收入變成廣告,這麼一來,在產業裡跳躍好幾個產業。應該看現在的產業到底怎麼做,根據這個模式進行研究,而不是列出一個框框往裡跳。
最後說一點感受,談到政策研究,很多政策為什麼出來,我是理解的,有時候我作為企業或者說作為一個消費者,我很苦惱。很簡單的一個概念,比如說手機,坦白講,我用的這個手機買的是水貨,到香港買的。為什麼到香港買?很簡單的大家知道,在國內的行貨由於政策的原因,wifi被取消,被禁止,但是wifi對消費者來講非常好用,非常重要,非常有革命性,突破性,我用得並不多,我只用收發e—mail、上網,並沒有用wifi—for,這個作為消費者來講非常好,非常重要的功能,政策上是被禁止的。
為什麼被禁止,我能理解很多原因。一種原因是衝擊電訊廠商的利潤,另外一種更冠冕堂皇的原因是害怕安全,還有一種深遠的原因是為wifi的自有標準留條路,甚至可能還有很多原因,但從消費者來講這些原因都不是理由。政策原因傳統來講有三個利益關係要平衡,國家、集體、個人,我們可以說個人更願意定位消費者,集體定義是企業,但是企業裡分很多種,尤其是現在最敏感的就是國企,因為國企容易變成運動員和裁判是一夥的,這就造成很多的問題。跟著國家利益這是比較敏感的話題,涉及到政策的問題,涉及到產業中長期發展的問題,涉及到社會穩定的問題等很多方面,但是我認為作為國資,國企利益方面,往往讓我們的政策變得非常完滿,我們到底要保護國資企業,保護國有資產,還是鼓勵行業競爭,還是讓消費者感受到最大的利益。很多的政策問題都出在這裡。我個人來講,對各方都理解,對國有企業也理解,對國家的政策難處也理解,對個人也理解,但是理解的基礎就造成作為消費者,或者作為產業裡的民辦企業,或者其他企業很大的痛苦。作為國企而言也很痛苦,作為政策制定來講也很痛苦,但是這個痛苦該怎麼解決,我不知道,還得看各位領導和老師,你們可能有更好的想法和主意。我只講這些,只是感受。